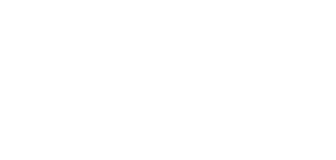栀子花开
小学 张军
两年前的九月,我踏着依然火热的阳光照射着的大地,走进了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的大门,成为了现在六(8)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对这个岗位,我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还记得,那些初见的陌生,它像极了孩子们对世界的问候,太过青涩。就是那简单的一句介绍,我们之间便有了熟悉的语言,我问你答,你说我听,虽然简单,但是我们都知道,那是成长的絮语。
转眼两年过去,时光见证一季又一季花与树的依依别离,岁月沉淀了一春又一春的娇美婉约。孩子们,我们要说再见了,可是这一句再见还没有说出口,往事就如同历久弥香的老酒,扑面而来。
一诺你记得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教室门口,你拄着双拐,因很吃力地爬到四楼而气喘吁吁、面色通红,却冲着我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那个笑容让我温暖了整整一天。清脆而洪亮的一声“老师好!”让我瞬间挺直了腰杆,哈哈,好幸福、好自豪的感觉。你知道吗一诺,面对你,我总是在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们无法抗争命运的安排,但是可以面对不幸从容地绽开笑容,让所有的苦难在磨炼中一笑而过,静静面对,默默守候,总有一天芳香四溢,让强大的命运也黯然失色。你脸上的笑容,让我老有一种错觉,好像过往种种的不幸,仿佛是别人的故事。虽然你在叫我老师,但你也在传递坚强和从容的意义,教会我得之安然、失之泰然。
还有你,梓峰,那天轮到你帮一诺打饭,从食堂出来,突下大雨,你脱下外衣把饭盒抱在怀里,一下子就冲进雨里。回到教室,头发上滴着水,我赶紧拿毛巾给你擦头:“傻孩子,用衣服先遮着头也行呀。”“没事张老师,包着饭盒饭就不会凉了,头发上的水,擦擦就干了。”看着你憨憨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是苍白的。拿了一张积分卡,作为奖励送给你,你连连摆手:“这怎么可以,张老师,这是我份内的工作,不需要奖励的,大家都做得很好。”我还是硬塞进你的手里,转身走出了教室。孩子,老师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我站在走廊的窗前,窗外大雨如注,你和一诺在教室内边吃边聊,欢快的笑声时不时地传出来,传出教室,冲向哗哗的雨幕中,如一道亮光,使雨点也在这光线的照射下,变得色彩斑斓,绚丽而又和谐。
蔡蔡和中睿,你们俩第一次搭档主持,是年级的游学汇报,原本只是觉得锻炼一下就好,没想到你们一出现就惊艳了全场。优雅的谈吐,时而细雨如织,均匀地洒落在地面;时而大雨滂沱,铿锵地敲打着窗棂。默契的眼神,彰显出谦谦君子的温和仪表;挺拔的身姿,勾勒出窈窕淑女的仪态万方。我坐在离你们不远的地方,时间定格了,空气凝固了。舞台瞬间无限延伸,在你们身后,在你们上方,放射出万丈金光,注定前路必定一路芬芳。那一时刻,镶嵌在我的记忆里,融化了冬雪,吹散了秋霜。
家萁,我真的好羡慕你可以有机会穿越西藏大北线。在布达拉宫脚下,你给大家寄来明信片,问候了全班每一位同学和很多老师,看到“很幸运可以在重要的时间遇上对我有帮助的老师”让我很感动。在纯净的蓝天下的那一片圣地,有人牵挂着我,这寄来的不仅仅是一张纸片,是孩子浓浓的一片情。
家豪,实在是令人意外,平时大大咧咧,不知忧伤为何物,却在诗词大赛上将一首《时间煮雨》演绎成了缠绵悱恻的离绪,让即将毕业的我们无限感怀。你满含笑意地谢幕,却让大家长久地沉默,余音绕梁的音符,带大家走进的不仅是生机勃勃的喜人天地,更是一处宁静安逸的心灵归宿,仿佛多么烦躁郁结的心情,都在这里变得云淡风轻,静美如初。
咱们班的super girl,只要你们参加比赛,就所向披靡,无功不返。我当然知道什么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你们牺牲了许多时间排练,每一个动作都细致入微,舞台上的精彩绽放是奋力拼搏的结果。可是当同学们向你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时,你们却红着脸低下了头,还相互偷偷地瞄一眼,露出犯了错误似的小娇羞,完全没有了舞台上的那点霸气和倔强。荣誉在那一刻是开在心间的一株丁香,淡雅清新,纯净馨香。
翻开纪念册,看到了你们拔河的照片。记得那一天,天气很冷,但是大家都不戴手套,说可以增加摩擦力。初场就遇上了上届冠军,那可是个劲敌。第一局我们输了,在交换场地的时候大家互相打气,又快速地调整站位,然后国元给大家做示范:“下蹲,绳子压低。”果然,对方很快感觉到我们不是很轻松就可以对付的了,双方进入了拉锯战。红绳在两个班之间游移,你们身体向后倒,有的同学已经没有力气了,依然努着劲把脸憋得通红,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当裁判的哨声响起,金晔还在闭着眼睛拼命。获得胜利后,你们全部瘫软在操场冰冷的草地上,搓着已经磨得麻木的手掌。芯悦捂着嘴大声哭起来,我轻轻地将你搂在怀里,今天就不劝你了,哭吧,孩子,眼泪不仅仅代表悲伤。拼搏、奋斗,极尽喧嚣又归于静谧,唯有你们的欢颜,在我眼前雀跃。那张照片,在须臾之间盖上了青葱邮戳,连同泪水一并寄给了逝水流年。
……
可是,还是到了“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的时节。读着王维的诗句,但闻眼前似栀子飘香。又是一年毕业时,在这淡淡的、涩涩的季节里,我将心中清晰的、模糊的记忆,都通过初夏这沁人的晨风,转化成这一季节里独有的素香,为你们送上深深的牵挂和祝福。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你们要搭另一班车去远方,整装待发吧。当你们走出校门的那一刻,我会在教室里,寻找一缕阳光,沏一壶清茶,捧在手,淡淡的茶香,弥漫在唇边,一人一景,独享乐声轻起——
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
二十一际遇
初中 李羊洋
这群孩子跟我一样,在校园的这一方小小天地,生活快满三年。旧的教学楼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这本大书里翻过去的一页,现在每天与同伴谈笑着踏入的,是优雅的初中部建筑群。四合的天井里,上了年纪的松树依然守护着我们的小日子。
我在这里仅仅待了三年,感觉却与这里的每一个人、一砖一瓦,像是相识多年。大概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久了,连呼吸和脉搏的节奏都会共鸣。三年前入职后便筹备着当时的新年级,前辈向学生气未脱的我描绘着“选课走班”的宏伟蓝图,我听着一些陌生的字眼,心里的教育情怀被迅速点燃。那种从无到有,赋予了我们这群“元老”类似造物的力量,你有了一个好想法,便会有人支持你去实现。
我知道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可以在一个以真挚、实干、肯付出为文化的团队里,得到了毕业后的第一把淬炼。入学教育有一个环节是“二十一探秘”,当时同年级组长和动漫老师说到儿时的一个游戏,几个孩子给另一群孩子设计一条藏宝路线图,终点是一个小小的奖励。我们三个升级了这个游戏,设计了第一版的“二十一探秘”。组长给每个老师定制了印章,动漫老师手绘了校园地图,所有的新生则需要去按图索骥,收集印章。当时我们都没有想到,新生们会有那么大的热情,在听完规则之后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现在再细细品味这段最初的经历,我不禁去想象,孩子们第一次听到、接触到、经历到“选课走班”带给他们的惊奇与新鲜时,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哈,我竟然也陪这帮小孩儿走过三年了。
我们80、90年代生人,其实与自己的老师并不亲密。老师对于我们而言,是一种很崇高、很遥远、很受人敬畏的存在,会严厉地要求学生遵守制度、认真学习。与现在的老师极大的一点不同,就是与学生之间的心灵距离。学生比当年的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成长的环境更为舒适和自由,这样他们对老师的要求也大大提高。我们做着类似班主任的工作,却在言行举止上更像精神和生活导师。因着环境和观念的巨大改变,我们似乎更容易走近学生,去实现全人教育。我会发现并且尝试去理解我的导师班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是那么不同。不论是哪一种教育方式,我的出发点都来自于对个体差异以及规则道德的尊重,所以三年积累下来的,是了解、关爱和成长的酸甜苦辣。我陪着他们长大,又何尝不是他们伴着我变成熟呢?我也曾戏谑班里四个调皮的孩子为“四大天王”,常常因为他们而生气、着急、彻夜难眠,可当其中两个转学的时候,我们和解,我也学着与心里那个不成熟不淡定的自己和解,那一刻百感交集,泪流满面。我伤心着别离,又为他们的未来默默祝福。
有时候觉得自己,最是嘴硬心软,打心底里热爱着这群不小心走进了我生活的小朋友。所以,那一路走来的,都是他们美丽的青春,我温柔的回忆:太阳底下的运动会、反败为胜的篮球赛、慷慨激昂的红五月、轻松快乐的游学、知识流淌的课堂、斗志燃烧的游戏、美味芬芳的文化节……我想,这里的每个老师都有着与我一样的心情,而学生们,也会记得这些时刻。因为学生活动不再是成套路的,老师指挥的活动。学生有自己的自主管理学院,一步步学会从台下走到台前,又从台前走到幕后,先体会了光芒万丈的青春绽放,而后懂得领导力和执行力可能比去展示自己的风采更能成就自己,也是成就他人。除此之外,每一次设计活动,我们会出谋划策,比如节日的意义、生日的庆祝方式、荣誉的涵盖范围、奖励的形式、学科的趣味化、活动的知识性等等,我们希望通过活动让学生对一些也许已经在他们脑子里僵化的活动形式和想法产生新的思索,考虑更多的可能性。学生们在这三年大大小小的活动里,既学习了如何做事为人,也学习了思考的方法和角度。
我在国外教材上读到的“以学生为中心”,竟在这所小小的校园里,一点一点得以实现,那么我们离理想中的二十一世纪未来学校,还有多远?当我们所有的成年人,真正能做到把学生视为一个值得我们绞尽脑汁创造最佳的用户体验、与我们无差别的社会公民时;当我们所有的老师,不再自己设计好了一切等学生做出我们期待的反应,而是敢于面对孩子们未知的反应与鲜辣的提问时;当我们所有选课走班的经历者,在这真实和丰富的体验中,尽情去享受、努力去创造、勇敢去改变,我想我们将会大大缩短自己与那理想和情怀的距离。
我想我的情怀就是,培养出有想法有理想的小孩。我觉得我所设计的课堂、活动、规则、每一次的谈话都出自于内心深处的这个教育哲学。初一的时候我努力维持着想象中老师的形象:稳重、严肃,我追求着课堂上的绝对安静,与爱说话的学生常常“斗”得两败俱伤。到了初二,学生对老师的“管”最不服气的年纪,我感觉自己尽了全力,但依然达不到想要的绝对安静,又如何去培养什么想法,什么理想?坦白说,我真的不是从没想过要放弃。挫败感曾一度深深击垮了我,令我疲惫和痛苦。如果不是前辈的帮助与开导,如果不是其他孩子带给我的慰藉,如果不是我尚能发现孩子们身上宝贵的品质,我肯定过不了这一关。我听过经验分享和讲座,看过班主任管理的书籍,观察和聆听过别的前辈,可这些远远不够,一个年轻的教师仍然需要亲自走一遭,要去直面那困难重重的现实,要在挫败中找到进步的机会,向前走,不断向前走。
最后,我那么多的困惑,都在一个学生转学后给我的留言里得到解答。我曾以为自己做着无用功,但是那些看似无力的教育瞬间还是在他心里留下了痕迹,他是懂道理的。我在看到他那么长的一段留言后,感慨万千,也终于相信“教育有力量”。现在这些孩子,哪个没有个性?面对骄傲的他们,我不再尖锐,而是更真实地站在他们面前,我不再端着老师的架子,我的情绪、疑问、劝解、告诫会摆在他们面前,也给他们选择的机会和判断的余地。当我把真实的自己诚恳地摆在他们面前,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更为鲜活的体验,我也真正明白了这份职业的意义所在。
这三年,每个学期结束,我都会给孩子们写导师评语,每句话都饱含我对他们的热情与热爱。三年里也收到过孩子们无数真挚的小作文,在彷徨的时分给予我无限的慰藉。这大概是最后一封,写给我亲爱的小孩的情书,在鲜花与泪光铺就的毕业大路口,祝你们的心愿早日成真,幸福提前降临。
2014年9月,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学校初中第一批“选课走班”学生入学。改革的浪潮将一位弄潮儿推上了风口浪尖。从前的她默默无闻,新的环境让她华丽转身,从前的她循规蹈矩,新的体制让她激活了潜能。薛靓,名如其人,青春靓丽、充满朝气。她走马上任,掌舵“选课走班”的航船,破浪前行。《时代教育》杂志记者曾采访她,写下这位“船长”真实的心路历程:
薛靓:我从不倦怠
沈立典 《时代教育》记者
薛靓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阳光洒满周围。她翻翻手上的资料,一会儿又拿出手机拨弄。但她可完全没有在玩,手机QQ打开全是工作群,一眼看过去十几个红点,微信里还有家长交流群。“现在办公很多事情都电子化了,处理起来快。”分分秒秒,薛靓都在解决问题。
薛靓从事教职的时间并不长,在教了两年初中英语之后,2014年9月,她成为了第一届选课走班制的年级主任。
“学校也是敢用我。”薛靓的表情生动,口气中带着惊讶,紧接着,“惊讶”转为“严肃”:“说实话,校长也需要胆量,按理说这个事儿应该是很有经验,很成型的老师来做才对。”
然而,在这件事上,哪里又有“很有经验、很成型”的老师呢?
“办法总比困难多”
“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自主学习’,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第一周,学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内容,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检测他,老师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但是慢慢地,就全都知道了,就是这样。”这是薛靓的感受。
与其在教研室里绞尽脑汁,不如直接面对学生一起来试试看“这样做会发生什么事”。而事实就是,没有那么难。或者说,对于薛靓来说没有那么难。
薛靓每天早上6点钟到学校。自己年级的学生这个时候已经在操场上“跑圈”,或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进行锻炼。但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的老师、年级主任和导师,她似乎总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学生呆在一起,她说自己很享受这个职业。
薛靓的能力更多来自于她的个性和从教后的经验积累。她学得快,做得多,并且好像不知疲倦:非上课时间,她在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处理,到了上课时间则去上课,似乎分秒不得歇。晚上,十一二点,她或许还在备课,每天如此。
今天薛靓有一点感冒,但她并不露病态,说话依然是快速明晰,刚把海淀区公开课听课事宜的电话挂下,又在楼道和老师商量下周运动会的班级出场介绍词。
多线程地同时处理几件事情,这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中一向被认为是优良的品质,薛靓就能做到,而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快速推进的教学改革也需要像她一样的老师。
薛靓没有痛苦的责任感,她觉得做好自己的事是理所应当:“教育是良心活。你备课怎么样,上课怎么样,有什么活动,做得如何,其实校长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他不可能追踪到每个老师那里去。”并不是畏于某种惩罚,没有什么东西在催促压迫薛靓,她就是觉得自己该做,她便去了。
对于薛靓来说,“去做、试试看”总是先于“这该怎么办”,她忽略掉了“难”的部分,专心做事,少想“有的没的”。她说:“不懂的时候也不算是困难,因为我觉得办法总是比困难多。” 薛靓总是一下子就能说出很多东西,唯独提到困难,她需要想一想,像是从很遥远的记忆里挖掘什么:“当时觉得有的老师是没有能力的,就是在我看来,但是通过这半年之后,我们这个年级的人带新一届的时候,都是抢着要的。他们本身的能力都在提高,然后会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然后再学习、再进步,就是这一年顶三年在用……”“原本,老师每年的工作其实是重复性的:带班、教书,但因为接受了新鲜的事物,点燃了职业的激情,然后每天在成长,对教育的感受有了不同,这种专业发展,能克服职业倦怠。”薛靓说,每位老师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尝试着自己的创新,没有时间去倦怠。
改变自然而然发生
“我们无法做伟大的事,只有用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小事。”薛靓不太记得这是自己在哪里看到的一句话。作为一个老师,“学生喜欢你、也喜欢这个地方,家长支持”,她就觉得挺高兴的。
这一届学生给薛靓的感觉是“特别活,特别不怕老师,你在与不在他都那样”,这或许与他们拥有大量的自主时间有关。
刚开始的时候,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的老师不知道“自主”的方圆在哪里,怎么给学生制定规则。上操,上自习,上课,学生都显得很慌乱。但是学校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接受这种状态,等待新的规范建立。一朝养成,很多问题迎刃而解。
学校的宽容态度,也让老师做起各种尝试来从容很多:“只要你想做,你有你的理由,那就去做。校长也会随时问问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很关心这个发展,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语文老师要做阅读推广,每晚的七点半到八点,半个小时;英语老师开设原声电影课程,让学生尝试英语配音,体验语言;国画老师的教室是她自己设计的,未来还要在天花板上和学生一起画上人物,临摹敦煌壁画……学校都放开手让老师去尝试,校长或许不能参与到各学科的专业思考中去,也会时常关心,却不加干预。
选课走班,不仅是给学生自由,也是给所有人自由,参与教育的每一方都要相互信赖,而这种信赖来源于自由造成的开放氛围。所有教学信息都敞开,逐渐地,教育的接受者——学生,他们也开始向老师家长敞开自己,表达自己。
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校的学生有很多活动,他们不停地锻炼,然后不停地展示。有一次活动需要学生去演讲,薛靓就和年级老师商量弄了一个年级的比赛:让每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我的成长》,然后进行了“《我的成长》演讲PK赛”,几轮下来,既练习了语文学科,又完成了任务。“你认为那是一个任务,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活动,你就知道这个事你要干什么,你不能为了达到目的去达成,有一些无奈的事情你可以让它变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做老师的一个特点。”薛靓似乎有点“工作狂”,好像把什么事情都揽起来做,但实际并非如此,她几乎从没有去给谁命令,她没有去“管理”这个年级,她只是参与到这个年级的每一件事里。
在以前,一个年级的主力是7位班主任。其他科任老师,只需要管好自己的学科,上好自己的课,这个年级什么样和自己没关系。因此,这些老师通常很被动,既没有去创造什么的动力,甚至因为和学生缺乏沟通,面对一群“陌生人”,连课堂都把握不好。
以前的时候一个年级的主力就是7个班主任,其他老师,例如一个科任老师,英语老师,那他只要判他的卷子上他的课,就可以了,这个年级什么样和他没关系,他只要把自己的两个班教好就可以了。学生其实很“懂事”,以往只有老师厉害,或者特别喜欢表达的孩子,会喜欢来跟老师沟通,而普通的科任老师,学生几乎“不搭理”,学生眼中只有班主任。于是其他老师上课会很被动,他既没有去创造什么的动力,甚至因为和学生缺乏沟通,他面对一群“陌生人”,连课堂都不太好掌握。
导师制实行之后,年级的所有老师要参与到年级事务中来,每位老师也都有了研发活动、开课、教研的自由。薛靓觉得:“这让教师真正成为了一个教育者。”老师掌握了主动权,感受到一种职业的尊严,还能收获和学生的良好关系。
就这样,通过一件件“小事”,改变自然而然发生了。学生会像大人一样讨论自己的事务,条理清晰,分工明确;老师却像小孩子,围绕着问题想出很多端头,总能找到新的东西,总是期待明天能创造些什么。
薛靓即是如此,就好像:她的每一天都被新鲜可爱的事物充满了,从来不觉得倦怠,也没有困难能够一直困扰她。
如今,三年过去了,到了检验改革成果的时刻,初三年级的师生正在全力以赴。他们想要大声宣告:“我们不仅会实践,不仅有能力,学业也很好!”期待他们的好成绩!